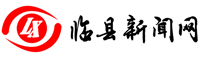|
 秦殿元近照
秦殿元近照
1940年阴历3月,日本人到临县扫荡,当时我还小,我于1924年生,日军来后我就是跟上大人们跑,到圪蟆里藏,1941年我当兵,在晋绥边区报名参军,我们弟兄4人,全家8口,靠老大(我哥哥)劳动度日。参军后我参加了青年纵队,和李德耀、李克楞一起,栓子、臭子都在41年牺牲了,我于1942年探亲回家。
当时下西坡住着我军35团,前身是决死四纵队,第二天早上说敌人包围了下西坡,我也随人跑到山梁,当时八路军没枪没子弹,被日军包围后,35团在西坡上当场死亡十八九人,损失很大。据说头天来了个卖炭的,其实这个人不是卖炭的而是汉奸,他从前村跑到后村、后村跑到前村,实际是在侦察,第二天早晨,敌人就包围了西坡,开了交手战。
严增明是原临县民政局局长,原在35团,在7连任指导员,在青塘与敌人打过一仗,在小园子35团把重机枪,团长连衣服都未穿好就逃跑,整个西坡地面小,小园子至探子沟,奶母梁三个地方共死了二十几人,当时民夫埋了这些战士,有的填入水渠、水窖,没有三天狼狗把这些人都刨出来吃了,人少了也不敢进地劳动,战士二十几、俘虏了四十几人,西坡村民死了2人。据说日军来后,李银儿(财旺父)藏在天桥窟窿里,日军喊话让他出来,八路在里头开枪,日在外开枪打死他。团长很抱歉,说对不起老百姓。晋绥青年纵队在岢岚、五寨等地抗日。
1942年,日军侵占三交,青年纵队改编成南临游击队,当时临县分为临南、临北,善庆峪、歧道、大峪沟属临南,我们安业属临北,下川与我们这一带通信不方便,就分为两个县与敌人打。我们的大队长叫朱治平,精兵简政后为临南游击大队长,吕运兴是一连连长,三连、二连是青年纵队改编的,我们二连指导员樊鸿吉,保护县队,天明听到枪响,出来被日军包围,指导员负重伤,我背上指导员就跑,眼看剩下三四十米,樊不用背了,硬让放下,后来放下他衣服脸部都被划破,这次俘虏了2人(一个是白文的当通讯员,一个是班里的兵),我们一直跑到枣窊。
日军在三交住,向日说话的是维持会的代表,送粮送草送钱,有的真服务、有的探消息。樊鸿吉(在三交烈士纪念塔上刻着其名字),日军让他投降,放下白面、大米、猪肉让他吃,他不吃,日军就一方面在政治上引诱,一方面让他办事,三四天后,日军看见樊坚决不投降,就把他绑在马上饿死,当时各村的民兵、县委、政府召开了追悼会。
又一次,我们住康家塔,哨兵说敌人来了快上山,敌人向我们打枪,敌人冲上来,连长刘玉书受伤,我也受伤了(左脚),现在还有伤痕,我就住下来养伤,不到二十天,自己想到前方去,结果跑步时伤又犯了,又返进医院,子弹从脚上穿过。
我们配合正规军,政委为李光照、朱治平是长征干部,李光照在临南游击队任副政委,政委由地方上的县委书记兼任。在窰家山侦察到日军小欧米茄白地圪垯过来,正规军的2个连都由李光照指挥,可能是敌人用千里眼(望远镜)看到了李光照,“啪”一声打到李的肚上,我背起李光照就跑,李光照是湖南人,他喊着“哎哟我的妈呀!”我们从井头下去,听不到枪响了,在李身上下找不到伤口,有个影子是从背上进的从肚上出来,结果李没气了。李光照牺牲后,在丛罗峪给他穿上新衣服,就地掩埋,后来听说尸首运回八宝山,西门外山上的烈士名单里有他。
与日军打,硬打无炮无子弹,当时毛主席号召把敌人挤出去,怎么挤?用肩膀挤吗?不是,挤就是说不要给敌人送粮送草,不当奴隶。配合正规军在义圪垛打,把敌人的司令官打死,对敌人来说政治上、军事上都是损失,一周后,一连的战士张应之被俘,日军为了给司令官报仇,把张绑在柱子上,用刀从头剐到脚,割的肉第一块献给司令官,非常残忍。
那个年代,我和战友们的责任就是保家卫国,都不求回报,唯一的愿望就是把日本鬼子早些赶出去。
“今年全国上下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,我的心情非常激动,虽然我已经91岁,赶上新时代社会,有吃有喝,子女们又孝顺,精心照料,天天锻炼身体、看报看电视,晚年生活得很幸福,很快乐。回忆起和我一起参军牺牲了的那些战友,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|